孑然遁入幽冥寻妻,一曲消融冥王的铁石心肠,却在重归阳间之际违约回望,就此痛失爱侣。奥菲斯的英雄悲剧令古今无数诗人唏嘘长嗟。“英雄”之所谓,是他的际遇不如神灵一般永久恒常,也不似凡人一般零琐日常,而是在命运和审慎之间漂泊跌宕。但也有不少哲人雅士不买奥菲斯的账。柏拉图,古希腊“疑诗”第一人,便对这位缪斯卡利俄佩的爱子冷嘲热讽,说奥菲斯更像是个懦夫,不愿自戕速死,与爱人在阴间团聚,而是苟且偷生地溜进地府,又因意志不坚,形影独只地离去。“失去幽灵真境界,幻来亲就臭皮囊”,最终死在色雷斯妇人手中,甚至心怀忿忿,为了不投胎转世为女性,宁愿做一只天鹅。

提香(Titian, 1490–1576)名作《奥菲斯与欧律狄刻》,同一幅画卷跨时空展现了欧律狄刻中毒而死、奥菲斯千里迢迢赶赴冥界的宏大叙事(约1508)

佛拉芒画家彼得·保罗·鲁本斯(Peter Paul Rubens, 1577–1640)描绘奥菲斯劝说冥王夫妇,从冥界领走欧律狄刻一幕(1636-1638)

丹麦画家克里斯蒂安·哥特利布·克拉岑斯坦(Christian Gottlieb Kratzenstein-Stub, 1783–1816) 描绘奥菲斯转身失去欧律狄刻一幕(1806)

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米歇尔·马丁·德罗林(Michel Martin Drolling)描绘奥菲斯转身之后失去欧律狄刻的一幕(1820)至于奥菲斯究竟为何转身,现代诠释褒贬不一,臧否各异。电影《燃烧女子的肖像》(Portrait d'unejeune fille en feu)中,贵族少女爱洛伊斯——她隐约透着十二世纪女哲人爱洛伊斯的个性——在火炉旁娓娓道来这段神话,女仆苏菲——良善可欺如卢梭《爱弥儿》之苏菲——惊诧之余,认为奥菲斯此举“毫无理由”。毕竟,按照“理性选择论”来讲,不论欧律狄刻的倩女幽魂在与不在,转身若非枉然,便会害得她“忽魂悸以魄动”,是有损无利的蠢事。但画家玛丽安——诚如象征自由解放的法兰西玛丽安——深受帕斯卡“心灵有理性不知之理”熏陶,认定是奥菲斯放弃了“爱人的选择”做出了“诗人的选择”,宁愿留下一瞬美好,也不愿意重返柴米油盐。最终,爱洛伊斯道出了她的“激进”观点:一定是欧律狄克要求奥菲斯转的身——施为性要着落在女性身上。剧末,爱洛伊斯叫住心碎逃遁的玛丽安,要求她最后转一次身:这种呼应不可谓不美妙。然而奥菲斯和欧律狄克团聚后,之所以涉险逃离冥界,必定是追求春回大地,而非永堕地狱。因此,“故意转身论”偷换了概念。“自求毁灭”或许规避了“选择存在”,但并不一定是真正的解放。

法国象征主义电影《燃烧女子的肖像》中,画师玛丽安像奥菲斯一样转身,隐约看见爱洛伊斯的影像与此相比,音乐剧《冥界》(Hadestown)不拘泥于个人选择,而着眼于社会批判,也顺道为奥菲斯平了反。地之阴司,幽冥境界,在这部音乐剧中成为经济剥削、社会异化的场域。人间正在经历气候变化、经济萧条,冥王劝道:只要加入冥界工厂,便无冻馁之虞。欧律狄克受到诱惑,与魔鬼签署了契约。她哀恸地唱道:“奥菲斯,我的心属于你,从前、往后,莫不如此。但我不能不管不顾,我的饥肠辘辘。”这个弱女子在隆隆汽笛声中被裹挟进运转不休的资本体系,我们难道该居高临下地怪她不饿死在“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”么?不是的。“命运”唱道:“来吧,怪罪吧!大谈仁义道德、罪孽深重。”“难道你是她,难道不会这样做?当你酒足饭饱时,当然可以秉持自己的原则。”此时,我们不禁想起,《指匠情挑》(Fingersmith)中十恶不赦的“绅士”瑞弗斯先生听到莫德谴责(狄更斯故里)兰特街贫民“卑劣”时,狠狠地把她揪出了院子,指着废墟咆哮道:“这才是‘卑劣’:贫穷!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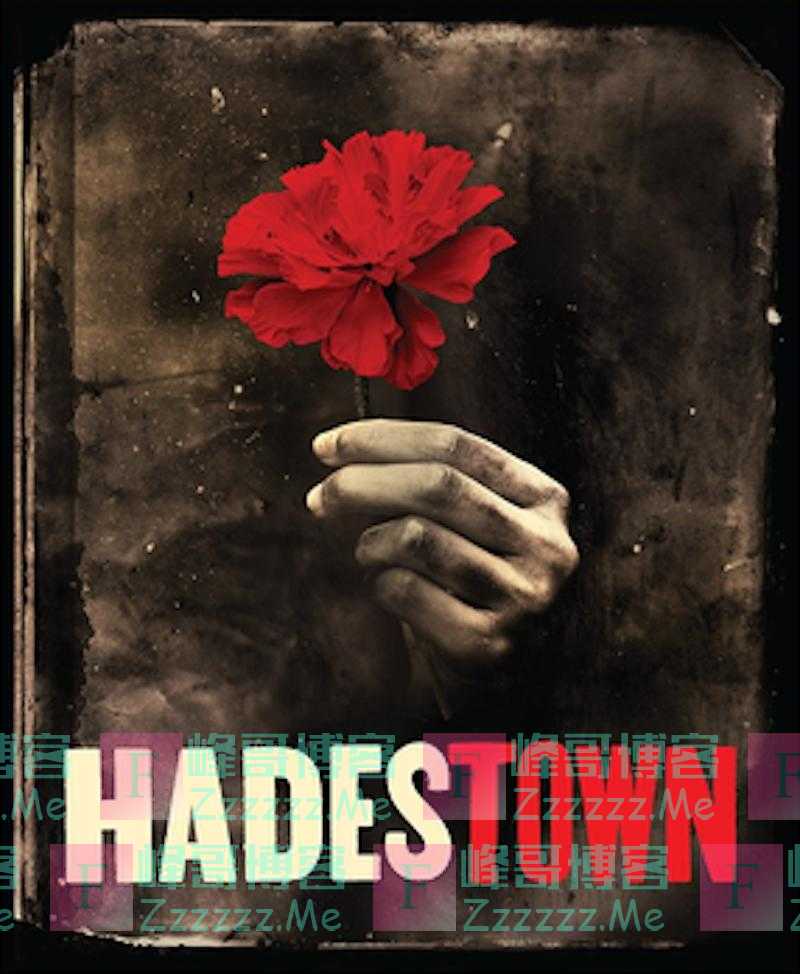
音乐剧《冥界》海报

音乐剧《冥界》剧照遥知香魂堕火窟,奥菲斯徒步下地狱,以歌声感化万千厉鬼。他也经历了短暂的精神危机。听说一切都不会改变:“唱歌徒劳无益,不论多么可怜。”他诘问自己:“被打压、遭背叛,再让人家告诉自己:什么都不会变?永远如此?”既然晓得湍流的方向,“何以还忤逆常规……何以还逆流泅水?”“何必淌水,汗流浃背?”如果注定徒劳,如果现存制度的不正义是历史上的必然,“为何还要斗争?”但他终于投入斗争,他的革命之歌回暖了地府冰冷的魂灵。而《冥界》中的冥王不只是一位压迫劳工的大工业资本家,更是社会关系异化的受害者。的确,他为富不仁地抱怨下层人民:“你施舍他们一片,他们却欲求不满;你指给他们一道缝线,他们会拆掉整个墙垣。”但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精神世界的干枯,甚至是艺术对政治压迫的颠覆:“你若侧耳聆听,王国便‘忽喇喇似大厦倾’……一曲亡国。”冥王自己呢?在冥界这样一个失去自然社会性的僵硬世界,他与曾经的爱侣珀耳塞福涅也同床异梦,渐行渐远。而奥菲斯穿透了冥界的城墙,像孙悟空一样大闹阴司,但他不是“轮着棒”,而是“唱着歌”。音乐触动人性意识,艺术激发政治想象:除了眼前的苟且卑微,还有什么可供替代的生活方式?这种艺术的穿透力打破了坚固的幽冥城墙——不是隔墙有耳,而是“墙也有耳”——也打破了多数受压迫者内化了的理所当然:在僵尸的世界里,他们已经对丧心病狂习以为常,但现在,他们开始怀疑。冥王颇有先见之明。当人民开始怀疑——除了维持现状,是否尚有其他可能?必须如此,还是别有所求?我是否可以追求?——地府的根本逻辑便已然颠覆了。但异化现象蔓延全部阶层,不只是直观上受到压迫的一方。资本家早已不再用皮鞭支配工人,但工人和资本家同时受到资本的支配。冥王表面上支配着地府,实则被这一令人窒息的空间支配。聆听着奥菲斯的歌声,冥王自己也在艺术中得到了解放。他和珀耳塞福涅重燃爱火,翩然起舞。
但冥界秩序不能朝令夕改,经济利益根深蒂固,尽管与这些激励结构纠葛不清的权威体系正在摇摇欲坠。冥王耳根虽软,悲悯众生,终究难以自断心脉。作为一位老年成功人士,他不愿铤而走险,“旧邦”不愿“维新”,旧制度的产物也不会革命。终于,这位与工人周旋多年的组织经济学实践者决定,此次仍由契约解决矛盾:奥菲斯可以带领苦力们走出地府——但他一旦回头张望,便前功尽弃,只能改良但不能被推翻的异化关系便会成为“永恒的、铁的、伟大的规律”。在希腊神话中,奥菲斯一路听不见、看不见,最后疑窦渐生,终于顾身。然而在音乐剧《冥界》中,奥菲斯是位“穷孩子”,缺少了乐神之子的光环,从踏上征程的第一步起,便开始怀疑自己:我是谁?我有何德何能,配为先锋党,领着人民重获解放?革命潜能怎能如此轻启?旧势力怎能善罢甘休?唾手可得的乌托邦,怎么可能实现在我们身上?终于,在革命者怀疑革命的声音中,他转了身,革命宣告失败。
信使赫耳墨斯登场,悠悠道来:“这是个古老的歌谣,这是个悲伤的歌谣……但我们仍然咏唱;知道结局如何,但依旧再唱。”——万一下次的结局不再一样?同样是旁白回溯历史,这段话不像音乐剧《巴黎圣母院》旁白回忆“大教堂时代”那样宏伟凄凉,但却恬淡地回归了日常。明知英雄悲而悲之,这是庶民的英勇。而奥菲斯的奉献是,“不论目前的现状,让你看清世界还可以是怎样”。诸神使者问观众:“你能看见吗?你能听见吗?”这趟地狱镇和乌托邦之间的列车,“它可是来了?可是朝着这里而来?”此时,市井气息的灯光和音乐慢慢复苏,观众仿佛经历了漫长时间,故事也已积起了灰尘,而灵魂的裂口似已愈合。在同样基于奥菲斯与欧律狄克神话的巴西电影《黑色奥菲尔》(Orfeu Negro)末尾,两个孩子坚信是奥菲尔的吉他每天清晨唤起了太阳。他们捡起了那把吉他,为了旭日重升,弹了起来。一个女孩采了一朵花,三人起舞。这大约是异曲同工的罢。英雄没落,歌声回归寻常人家。正如冥界国母珀耳塞福涅所言:即便人间的确该亡,但在那之后,大地再焕新生,太阳依旧升起。

经典电影《黑色奥菲斯》海报《冥界》辞曲时而可商,隐喻时有不章,但其社会批判在众多百老汇电影中即便不是独树一帜,也是凤毛麟角。《屋顶上的小提琴手》(Fiddler on the Roof)讲述犹太贫民虽然饱受欺凌,仍不懈追求人道精神,《西贡小姐》(Miss Saigon)歌颂平凡女性以强大的意志力逆着时代悲剧而行的人性光辉。而《冥界》批判的是一个麻木不仁却又浑然不觉,看似解决温饱问题实则侵蚀人性的社会体系,而它褒奖的不是那位意志薄弱、功亏一篑的年轻人,而是重新想象世界的勇气。《冥界》问世之初的十年间,鲜受关注。直到重新编导之后,在多事之秋的2016年登台百老汇,才一炮打响,经久不衰,一举斩获八项托尼奖,其中导因与辅因交错混杂,但少不了当代美国的政治语境。《冥界》第一幕最后一首歌《我们为何筑墙》恰巧讽刺了特朗普总统在墨西哥边境“筑墙”的口号,而贯穿全剧的爵士乐又恰到好处地代表了非裔音乐文化。但这些移民政策和种族文化的元素无疑是《冥界》最简、最浅、最显的洞见。奥菲斯功败垂成,有史以来无数变革也轰轰烈烈地倒塌了,但从地狱城到乌托邦仍然有一条崎岖幽暗的路。这段路,我们又该怎么走?在《哥达纲领批判》末尾,抱病在身的马克思意味深长地借用一句天主教祷词“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”(我已说出来了,已拯救了自己的灵魂)结束全篇。追忆奥菲斯,或者说,作为奥菲斯,我们大约可以说:“cecinimus et salvavimus animas meas”(我们已经歌唱,已拯救了我们的灵魂)。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文章如无特别注明均为原创!
作者:
F_Robot,
转载或复制请以
超链接形式 并注明出处 峰哥博客。
原文地址《
李汉松|音乐剧《冥界》:地狱城与乌托邦》发布于2022-3-10
若您发现软件中包含弹窗广告等还请第一时间留言反馈!
小米手机无法安装请到设置->开发者设置->关闭系统优化,安装后再开启系统优化。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