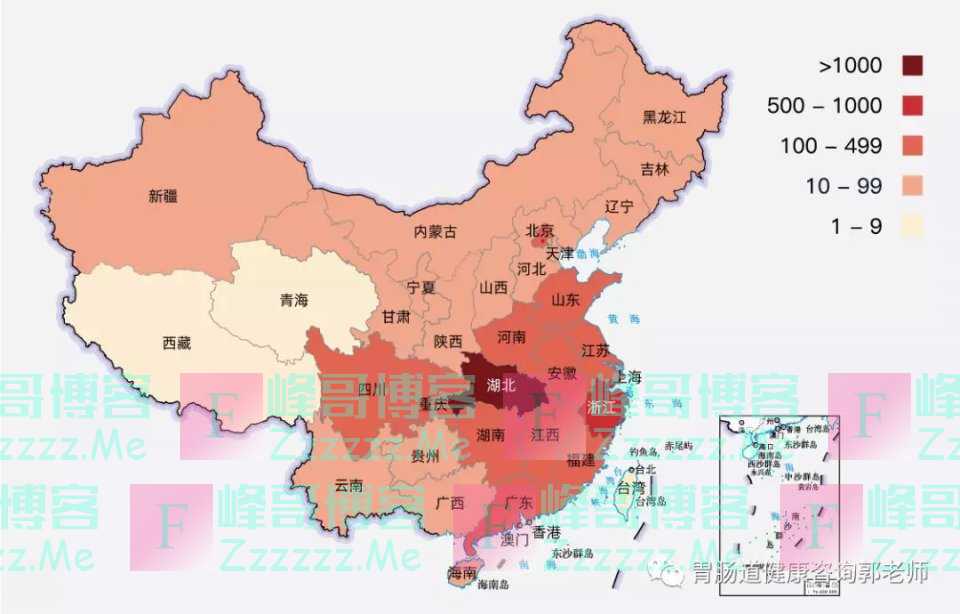视觉中国 供图
早些时候,母亲买了台洗衣机,小天鹅牌的。洗衣机装在如我一般高的纸箱子里,被放置在屋子的偏角里。在我看来,洗衣机是一种特别的存在,它是与生活质量挂钩的。我常幻想着它骨碌碌转动起来,将我们的衣物洗得干干净净。
母亲似乎忘记那台洗衣机了似的,仍旧提了塑胶的大盆子往龙头旁去,就着洗衣粉揉搓换洗的衣物。我年纪尚小,虽不解其意,但不知从何问起,只觉母亲做的便是对的。
凛冬来的时候外头冷得紧,纵使将门窗封得严实也抵不过刺骨的寒气。我们接上热得快,将它泡入水桶中,瞧着它在水底缓缓冒出气泡,不一会儿工夫,水便热起来了。我们挤在床沿,身上裹着绣花棉被,脚浸入热水里,一齐看着每日剧场的抗日片。令我奇怪的是,母亲仍旧坚持手洗衣物,顶冷顶冷的天气也不过是往盆里加一壶热水。
“你怎不用洗衣机?”我问。
“这天也不是那么冷。”母亲向来犟嘴。
“当我看不见你冻红的手吗?”我嗔怪道。
“从小做惯了的。”母亲一面说一面垂着头浣洗衣物。
“打开那洗衣机吧。”我说。
母亲拧开了水龙头,水柱汩汩往下流,径直没入盆里,在衣物上打出水花来。
她似乎没听见。
“打开那洗衣机吧,这是该用的时候了。”我又说。
母亲抬起头,汗水濡湿了她额头的发丝。她将那缕发丝撩拨至耳后,眼睛定定地看着我。
“现在还不是时候。”母亲说。
“莫不是夏天用?”我有些气急。
“倒也不是。”母亲说着,打量了一番我们所处的居室,“只是觉得不合适。”
“怎么跟供起来似的。”我嘟囔道。
“待我们住进新房子,到时候权当新家具用,岂不是光彩些?”母亲轻柔地说道。
“你总是有理的。”我撇撇嘴。
后来乔迁新居,三室一厅,虽不大,但足以让人欢欣。
那日来了许多亲戚,他们拎着甘蔗提着发糕吆喝着往里走,好不喜庆。阿嬷送的八仙桌也被抬了进来,据说这是阿嬷的陪嫁物,但后来阿嬷怎也不认,人们也就渐渐忘却了。
一起搬进来的还有那台洗衣机,小天鹅牌的。
“可以拿来用了吗?”我问。
“夏天手洗衣物可以清凉些,也可以省些电。”母亲一本正经地说道。
后来我便到中学去寄宿了,中学里常补课,每周仅有周日半晌得以休憩,我不想麻烦母亲,便总是等到月底才让她来接我回去。
母亲觉得我学习任务紧,在中学期间她从不让我洗衣服,只说是有洗衣机,不麻烦。我一门心思全在课业上,也就不再说什么。
毕业的时候,我同母亲一齐将行李物什搬回家中。在杂物房的角落里,我又看到了那台洗衣机,用塑料长条捆着的,小天鹅牌的。
“我以为你拿出来用了。”我说。
“我在镇上,你在学校,放在家里也不过是闲置的,与其让它平白无故吃灰,倒不如藏着放着实在些,也不必损耗它的寿命。”母亲说得头头是道。
再过些时日,我又升了大学。
收拾行李的时候,我又瞧见了那台放置在角落里的洗衣机。
“往后你双休日回来,便把那洗衣机拆出来用吧,再不用恐怕是老化了,白瞎那几百上千块钱。”我叮嘱母亲。
“会拆的,会用的。”母亲连连点头。
许多个假期里,阳台上那个为洗衣机设计的专属位置仍旧是空缺的,久而久之我也渐渐忘却了这台洗衣机的存在。
某一天,小区里来了个收破烂的老头,于是母亲与我一齐到杂物房收拾可以回收的废旧。
“那个箱子也抬下去吧。”母亲指了指角落那个洗衣机的包装箱。
“洗衣机你拿出来了吗?”我问。
“前些年就拿出来了。”母亲说。
“怎不见你用它?家里似乎没有它的存在。”我说。
“送人了,反正用不惯的。”母亲说。
我沉默片刻,将那洗衣机的包装箱拎过来,狠狠地踩扁了。
看见收废旧的老头渐渐远去时,我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,像是什么东西从我的生命里离开了。
某一个新年,我同母亲到小姨家拜年。
在她们寒暄的空当,我打量起小姨的家来,彩电、冰箱、空调,以及一台洗衣机,小天鹅牌的。那是很老的一款洗衣机,我看了看它的标志,是2013年的。它是那般老旧,老旧而小巧,小巧得有些小气,丝毫体现不出生活质量。
回去的时候,我问起小姨家的洗衣机来。母亲很淡然地肯定了我的猜测。
“我们家都没用上的。”我说。
“小姨比我们更需要的。”母亲说,“那时候她坐月子,男人不在身边,又沾不得凉水……”
“我们家都没用上的。”我只是重复着这句话。
那天回家的路上,我们一句话也没再说。
责任编辑:曹竞 毕若旭
来源:中国青年报客户端
文章如无特别注明均为原创!
作者:
F_Robot,
转载或复制请以
超链接形式 并注明出处 峰哥博客。
原文地址《
洗衣机(小说)》发布于2021-11-13
若您发现软件中包含弹窗广告等还请第一时间留言反馈!
小米手机无法安装请到设置->开发者设置->关闭系统优化,安装后再开启系统优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