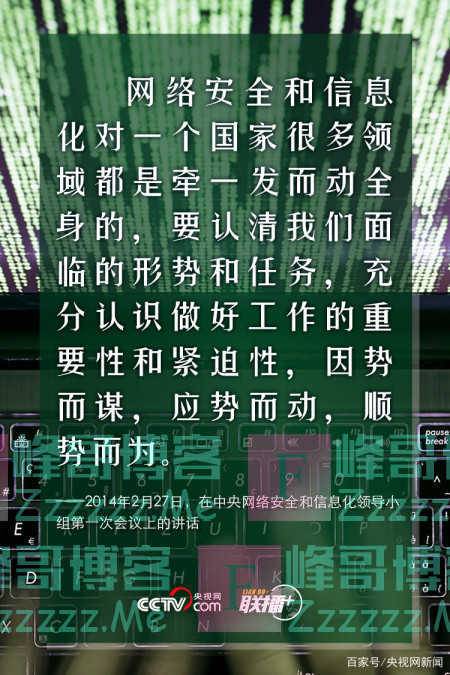文 | 孙克艳
我的老家在豫西南,一年收两季庄稼。6月初收割冬小麦,秋季收获黄豆、玉米、花生、红薯等作物。被遗落在田野的粮食,若是没及时收拾,就会发霉变质,造成经济损失,让人心疼。何况,乡邻们最是明白“粒粒皆辛苦”,他们对脚下的土地,和土地上的庄稼,有着深切的眷恋和敬畏之情。因而,庄稼收割后,大人孩子都要忙里偷闲,在已经收割过的地里“溜一溜”,淘淘宝。小时候,每年的两次收割季里,中小学都要放假:老师们回家收庄稼,孩子们回家溜庄稼。

拾麦穗是一件简单却不容易的事。大家顶着炎炎烈日,被炙烤的热浪包裹着,一边着箩筐,一边弯着腰眯着眼,巡视着广阔的土地。当攥在手里的麦穗多了,就用麦秸秆捆扎好放在筐里。一捆捆扎好的麦穗,像是光荣劳动得到的奖章,骄傲而盎然地挺立着。一天下来,勤快的人总能拾几斤、十几斤麦子,甚至更多。孩子们拾来的麦子,要放在一边单独碾出来,过秤约了,报个数。这个数字,是对孩子们的劳动的总结,褒奖都在里面了。这个数字,会让孩子们记很久,甚至是一辈子。
相比拾麦穗,秋季溜庄稼可就有趣多了。那时候,天高气爽,风轻云淡。加上秋季庄稼种类多,溜庄稼的快乐,也更丰富些。大家相伴着,带着工具,逮住什么溜什么。收割过的黄豆地,露出一排排整齐尖锐的根茬儿,一不小心,就会戳破鞋子扎到脚。即使穿上千层底布鞋,也得加倍小心。这时,黄豆地里,总有很多成熟的麻包蛋,鹌鹑蛋大小,黄澄澄的,散发着诱人的果香。咬开,酸中带着香甜,是孩子们喜爱的野果之一。溜苞谷(即玉米)对不少人,特别是皮肉娇嫩的孩子来说,是一件苦差事。溜苞谷的时候,每个人拿一个蛇皮袋,一边走一边拎着。
稠密的苞谷地里,空气是凝固的,闷得人透不过气。而苞谷秆和叶脉又带着一层毛,刺挠得人难受极了,又痒又疼。钻出地,站在空旷的田野里,顿时觉得自由的呼吸和凉爽的风,竟无比惬意。溜花生时,带一个蛇皮袋或竹筐,和一个小钉耙。蹲在地上,先用钉耙刨。灰黑色的土地上,刨出来的白色花生很是显眼。馋嘴的孩子,总是控制不住想要填填嘴巴。溜花生时,若是逮住一个老鼠洞,刨开来看,里面必定有白花花的花生。
我印象最深刻的,却是母亲跟随邻居,骑车去几十里外的沙地溜花生。那时候流传着一个说法:花生只能在沙地上种植,我们家乡那边的岗地不适合。因此,那几年深秋,母亲一忙过农活,就带着干粮和水,跟大家骑车去沙地溜花生。天擦亮就出发,披星戴月赶回来。那些饱含着母亲辛劳的花生,晒干后被悬在屋顶,等到过年时,才舍得拿出来,炒熟了,让大家开怀吃。后来,随着花生的广泛种植,大家就不用跑远处溜了,能把自家地里的花生溜干净,就不错了。
溜红薯就是一件大体力活。这活,孩子们干不来,干了也不长性。在乡约里,溜庄稼的人,只能待在已经收获的土地上,不能去尚未收获的庄稼地里。瓜田李下,泾渭分明。因为,一个叫溜,一个叫偷。而收获过的地里,须得主家允许,才可以去溜庄稼,因为颗粒归仓,是庄稼人的愿望。在广阔的田野上,溜庄稼的人,零星地散布着,点缀着显出本色的土地,像一个个辛勤的蚂蚁,寻觅着田间遗落的粮食。肩头上或筐里,那或多或少的收获,都是对土地的回应和敬重。
现在,日子好了,很少有人会揣着当年的热情,起早摸黑溜庄稼。那些被遗落在田间的粮食,或是沤烂发霉,或是出芽长成野草。而我已经有二十多年,没有溜过庄稼了。那些关于溜庄稼的往事,就像曾经吃过的麻包蛋一样,逮住一个,就扯出了一条藤。
壹点号山东创作中心
文章如无特别注明均为原创!
作者:
F_Robot,
转载或复制请以
超链接形式 并注明出处 峰哥博客。
原文地址《
难忘幼时溜庄稼》发布于2021-9-28
若您发现软件中包含弹窗广告等还请第一时间留言反馈!
小米手机无法安装请到设置->开发者设置->关闭系统优化,安装后再开启系统优化。